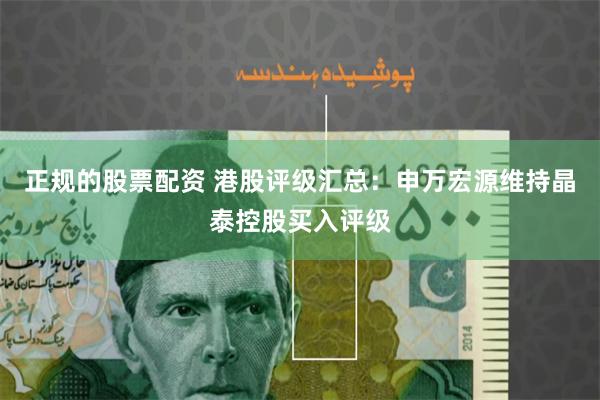当我们在课本、影视剧乃至日常谈论中提及大汉王朝的开创者时股票配资好做吗,一个称谓几乎脱口而出——汉高祖刘邦。
这个称呼是如此根深蒂固,仿佛从两千多年前便如此确定无疑。
然而,当我们翻开最权威的汉代原始记录,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赫然呈现:刘邦本人从未被正式尊为“高祖”。
这个流传千古的称谓,竟是一场持续近两千年的集体口误!
一、铁证如山:史册记载的刘邦真名号若要探寻真相,必须回到最接近那个时代的原始档案,即被历代奉为圭臬的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。
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,为刘邦立传的篇章,明确题为《高祖本纪》。开篇即云:“高祖,沛丰邑中阳里人,姓刘氏,字季。” 通观全篇,“高祖”一词频繁出现,似乎奠定了基调。
展开剩余86%然而,就在这部本纪的后半部分,司马迁清晰地记录了刘邦去世后,朝廷为其议定名号的过程:
“群臣皆曰:‘高祖起微细,拨乱世反之正,平定天下,为汉太祖,功最高。’上尊号为高皇帝。”(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)班固的《汉书·高帝纪》同样忠实承袭了这一关键记录:
“群臣曰:‘帝起细微,拨乱世反之正,平定天下,为汉太祖,功最高。’上尊号曰高皇帝。”这两段出自汉代核心史籍的文字,指向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:刘邦死后,群臣一致尊奉他的庙号为“太祖”,谥号为“高皇帝”。
这才是汉朝官方给予开国皇帝最正式、最准确的名号组合——汉太祖高皇帝。
二、迷雾初起:司马迁笔下的“高祖”疑云既然朝廷定论是“太祖高皇帝”,为何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却处处称其为“高祖”?这是否是称谓混乱的源头?
细读《史记》,司马迁在涉及刘邦生前事迹时,常用“高祖”指代。例如,描述其早年经历:“高祖为人,隆准而龙颜,美须髯”。
记载楚汉相争关键战役时:“高祖之出荥阳……高祖复军成皋。”甚至在记录其临终安排时:“高祖击布时,为流矢所中,行道病。病甚……已而吕后问:‘陛下百岁后,萧相国即死,令谁代之?’上曰:‘曹参可。’问其次,上曰:‘王陵可。……’” 这里,刘邦生前自称“吾”,而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则称其为“高祖”或“上”。
关键在于,“高祖”并非司马迁凭空捏造或误写。
他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解释:“汉兴五世,隆在建元…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,王迹所兴,原始察终,见盛观衰,论考之行事,略推三代,录秦汉,上记轩辕,下至于兹,著十二本纪,既科条之矣。” 可见其著述宗旨在于追溯兴衰脉络。
对于本朝开国君主,他采用了一个在当时可能更流行、更能体现其开创性地位的尊称——“高祖”。
这个称谓,在司马迁时代或许带有“功业最高之先祖”的强烈褒扬意味,是史家基于其历史地位的一种“尊称”,而非严格遵循其死后的官方庙号。
三、称谓流变:“高祖”的固化与普及“高祖”称谓虽非官方庙号,却因其在《史记》中的广泛使用,影响力与日俱增。
班固著《汉书》,虽在关键处保留了“为汉太祖”的原始记录,但在全书叙述中,绝大多数时候也沿用了“高祖”这一称呼。
其开篇即为《高帝纪第一》,记载刘邦事迹时写道:“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……高祖隐于芒、砀山泽间。” 这种处理方式,无疑极大强化了“高祖”在史书叙事中的主导地位。
到了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,这部旨在“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”的编年体巨著中,“高祖”更是成为指代刘邦的标准称谓。
开篇第一卷《周纪一》之后,第二卷即名《汉纪一·太祖高皇帝上》。司马光在正文中叙述:“初,高祖不修文学,而性明达……” “高祖悉去秦苛仪,法为简易。”
尽管在卷首标题谨慎地并列了庙号“太祖”与谥号“高皇帝”,但在实际行文中,“高祖”以其简洁和极高的辨识度,成为最普遍的选择。
这部作为后世帝王教科书和士子必读的史书,将“汉高祖”的称谓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层面。
四、名定俗成:“汉高祖”为何深入人心官方庙号“太祖”为何不敌史书中的“高祖”?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逻辑。
“太祖”作为庙号,严格用于皇家宗庙祭祀体系,是极其庄重但相对封闭的礼仪性称谓。而“高祖”一词,天然带有“王朝基业开创者”的崇高光辉。
蔡邕在《独断》中论及庙号含义时曾指出:“太祖,功最高,德及于后代。” 这恰恰解释了“高祖”称谓在民间乃至史家笔下的巨大吸引力——它直白地指向了刘邦作为汉朝开创者的核心功绩与历史定位。
班彪在《王命论》中赞颂刘邦:“高祖……奋臂于陈、项之间,讨乱除暴,克复帝业……盖在高祖,其兴也有五:一曰帝尧之苗裔……二曰体貌多奇异……三曰神武有征应……四曰宽明而仁恕……五曰知人善任使。”
这种对开国皇帝功业、德行、神异与能力的全面推崇,与“高祖”所蕴含的“至高无上之先祖”的意象完美契合。
当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经典史籍反复以“高祖”称呼这位开国之君,当《资治通鉴》将其作为标准表述,“汉高祖”便在官方正式称谓之外,开辟了一条更为强大的民间认知和话语传播通道。
它超越了宗庙的藩篱,成为了一个象征开国伟业、代表汉朝源头的文化符号。久而久之,约定俗成的力量彻底压倒了最初的庙号制度。
“汉高祖”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接受度,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对刘邦最响亮、最普及的称呼。
五、余响:史笔与民心交织的称谓传奇从汉廷庄重议定的“太祖高皇帝”,到司马迁笔下那个充满开创气息的“高祖”,再到两千年约定俗成的“汉高祖”,刘邦称谓的演变,是一部官方礼制、史家笔法与民间认知相互交织、共同塑造的历史。
班固在《汉书·叙传》总结高祖功业时写道:“皇矣汉祖,纂尧之绪,实天生德,聪明神武……讨暴秦,诛强楚,为天下兴利除害,继五帝三王之业,统天下,理中国。”
无论称其为“太祖”、“高皇帝”还是“高祖”,其中蕴含的对这位布衣天子扫平群雄、一统天下、奠定四百年基业的崇敬,始终如一。
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,一个最初并非官方最准确称谓的“高祖”,因其最能彰显刘邦作为王朝开创者的至高地位,因其在最具影响力的史书中的反复书写,最终战胜了礼官们精心拟定的庙号,牢牢占据了后世亿万人的心智。
这并非历史的谬误,而是史册记载的强大惯性、语言传播的内在规律以及民众对开国英雄朴素敬仰的共同结果。
当我们今天依然习惯性地称其为“汉高祖”,我们不仅是在称呼一位帝王,更是在复述一个由太史公起笔、被历史长河反复书写、最终烙印于民族记忆深处的传奇故事。
这个“美丽的误会”,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独特篇章。
发布于:山东省